
第1章 心灵的电波
一名15岁男孩的头部遭到枪击——历史没有记下该事件的细节,但它的结局却改写了历史。因意外枪击而留在男孩脑中的子弹无法通过手术取出,这造成他一侧身体瘫痪,并终身被眩晕折磨。男孩虽幸免于难,但枪伤使他缺了一块颅骨。后来,他被送往德国耶拿的一家精神病院。他的医生汉斯·伯格想要的正是这样一个病人。让伯格医生感兴趣的不是这名当时已经23岁的男子的精神状况,而是他头上的那个弹孔。
透过颅骨
1902年11月,伯格迫不及待地让人将这个年轻人带到精神病院底层的实验室进行单独研究。该男子是否以为这是某种针对他的治疗方法,我们不得而知。现在我们知道的是,伯格医生(他于1919年成为该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并没有把所有人的生命都视为同样神圣的。
那个年轻人按照指示坐在椅子上,瘫痪的手臂悬在一侧。他感觉到被人从身后揪着头发,听到剪刀的咔嚓声。他听见水声和木杵撞击陶瓷杯发出的空洞的声响。过了一会儿,他的脑袋就被涂上了肥皂沫,散发着浓烈的辛辣气味。满是泡沫的剃须刷让他觉得无比温暖。伯格医生用剃刀一下一下慢慢地剃掉了年轻人的头发,然后用毛巾擦干他的脑袋。伯格特别留意头部伤口周围的区域。那里由于缺失一块颅骨而留下了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洞,只有薄薄的皮肤和疤痕组织覆盖在上面。

图1 汉斯·伯格的实验记录本记载了他在20世纪初所做的关于精神能量和身体能量之间关系的实验。在伯格的患者中,有的颅骨缺损了,缺损的部位仅被一层皮肤覆盖,这使伯格能够监测大脑随着感觉刺激、药物、体位和情绪的改变而产生的容积变化
伯格医生在这个洞上安装了一个用古塔波胶(一种天然橡胶)做成的样子很奇怪的帽盖,并将帽盖连接到充满液体的橡胶管上。这套装置类似于压力计,可以用来测量大气压力的变化。伯格医生小心地把橡胶管和帽盖上的接头连上并密封好,以确保不会泄漏。管子的另一端与旁边桌上的一个设备连接,这个设备的滚筒上悬挂着一根锋利的金属笔。帽盖和橡胶管连接好以后,只要缓缓转动滚筒,金属笔就会在滚筒带动的炭粉纸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色痕迹。
当血液被泵入黏稠的脑组织中时,大脑会稍微膨胀,然后又略微回缩,就像气喘吁吁的狗的胸部一样。这个年轻人的大脑随着心跳的节律而膨胀和收缩,橡胶管内的液体也随着头部伤口处的微小压力变化而上升和下降。同时,它们所连接的记录设备通过微微颤动的金属笔在滚筒纸上留下了锯齿状的、间隔规律的纹路。伯格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波浪线——多亏这个缺了颅骨的“窗口”,伯格才可以观察到大脑的脉动——这使他兴趣盎然。
伯格医生并没有为这个年轻人提供治疗,他的目的并非要了解患者的病情,也并非要缓解他的精神或神经功能障碍。伯格的兴趣在于检验他自己的一个理论,即人的心理状态与大脑内部的物理过程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在那个时代,人类心理的起源和机制以及一般的心理功能仍然是个谜。因此,伯格的理论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尽管年轻人的大脑搏动与他的心脏搏动同步,但是大脑搏动的幅度却时强时弱。伯格认为,这些振幅的变化与大脑组织正在进行的思想和情绪活动有关。他把这些观察结果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之后在1904年的专著中发表。[1]这种大脑搏动会受各种药物和身体姿势变化(坐、站立或头部向一侧倾斜)的影响,这些都不足为奇。对于伯格而言,更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大脑搏动形成的波浪线也会因思索、情绪和感觉输入的变化而改变。除了这名年轻人,伯格还在其他归他管理的患者身上,利用各种刺激方法和认知方面的测试做了类似的实验:他让患者伸出舌头,然后把糖水、柠檬水或奎宁(味道非常苦)滴到他们的舌头上,以刺激味蕾;他还用含有各种刺激性物质的棉球凑到他们的鼻孔下,或者让他们闻装有胡椒粉或其他香料的小瓶;他用一支很细的画笔在患者的手、胳膊和脸颊上轻轻画线。做每个实验的时候,伯格始终盯着那条在滚筒上画出的波浪线,观察受试者脑部随血流进出而产生的膨胀和收缩。通常,伯格施加的这些刺激会扰乱大脑搏动的正常节律,这让他更加相信,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例如味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与生物和物理过程之间是会产生相互作用的。

图2 汉斯·伯格使用体积描记仪研究一名颅骨缺损患者的脑容量波动
伯格怀疑人类的情感也是以身体作为物质基础的,因此,他相信这个脑容量监测装置(或称体积描记仪)可以记录喜悦、悲伤或恐惧所引起的反应。人类的情感只能在人类身上进行研究,伯格正是要利用这名年轻人的大脑来检验他的理论。他悄悄地走到这名男子坐的椅子后面……突然开了一枪。枪声震耳欲聋。自从头部遭受枪击以来,这名男子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此刻,这名可怜的年轻受害者立刻陷入惊恐和休克的状态。伯格看到强烈的恐惧心理状态导致脑循环迅速减少,这令他激动万分。他在1904年和1907年出版的两部专著中分两部分详细介绍了他的发现。这两部专著的题目都是《精神状态的物理表现》(über die K?rperlichen ?usserungen Psychischer Zust?nde)。[2]
此后,伯格继续对脑压变化进行研究,并将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大脑的电活动。他是第一个进行人类脑电图(EEG)实验,第一个发现并记录人类头部发射出的电波的人。他所开创的技术和方法让科学界第一次看到人类思维运转的过程。
伯格的发现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你一定会认为他的名字将被写进教科书吧?但是相反,他始终是个像影子一样模糊的人物。为什么?很不幸的是,用患者进行实验的做法在伦理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使伯格在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研究领域中很难出人头地。那么,汉斯·伯格是谁?他是如何取得这个举世震惊的研究成果的?
耶拿之旅
我去了德国耶拿市,想亲自找找看,一个世纪前在这里工作过的伯格可能还会留下点儿线索。耶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后被苏联划归民主德国。柏林墙倒塌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最终恢复为民主的、统一的德国,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那以后,耶拿便开始衰落。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会随着政治变革而扭曲,而重建历史真相必不可少的天然和人工物证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落、丢失或遭到破坏。伯格是一个谜。我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以便更好地理解脑电波这一大脑基本特征的发现。
一座中世纪的石头教堂数百年来被煤烟熏得发黑,像玛雅人的庙宇一样被枯萎的藤蔓缠绕着。在教堂后面的一片空地上,我发现了一座坟墓,它乍一看只不过是一个长满常春藤的绿色凸起。大树遮挡了阳光,坟墓四周环绕着常春藤和蕨类植物,粗纹花岗岩墓碑上面刻着伯格的名字,短短两个日期就概括了他的生平。铭刻在石头上的字被漆成黑色,与灰色的墓碑形成对比。在墓地的一片寂静中,伯格仿佛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真实,而不再是一种历史的抽象。他,作为人类一员的汉斯·伯格,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就被埋葬在我面前的这片土地下。伯格的儿子是一名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苏联战死,当时距伯格逝世只有几个月。
我离开墓地,步行到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解剖大楼,与神经解剖学家克里斯托夫·雷迪斯及其同事、历史学家苏珊·齐默尔曼见面,前者同意将我带到汉斯·伯格工作过的精神病院。在大学走了一小段路后,我们来到了一栋现在以伯格的名字命名的建筑。那是一栋被刷成黄色和红色的三层砖砌建筑,天窗从高耸的屋顶凸出。那栋楼正在翻修,没有人居住。外面的门有两扇朝外敞开着,门前是伯格医生的半身像。冰冷的石头雕像跟伯格那一本正经且严肃的容貌很吻合。

图3 汉斯·伯格在德国耶拿的坟墓。他与妻子乌尔苏拉和儿子克劳斯埋葬在一起。墓地离伯格工作的精神病院(他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人类脑电波)不远
伯格在这里工作了30年,致力于寻找肉体(大脑)和精神(精神能量)之间的边界。他孜孜不倦的探索最终指引他从研究血流和脑容量,逐渐拓展到研究一种在20世纪初令科技和社会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能量——电。伯格开始投身科学研究时,还身处一个靠马车运输、靠煤气灯照明的时代,到他结束科学生涯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了电灯、汽车、飞机、无线电和原子裂变。在此期间,对人类大脑的研究也从哲学和心理学的根基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把显微技术应用于细胞分析,把生物化学应用于化学成分分析,并使用电子设备研究神经组织的电学特性——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神经科学。
在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另一栋建筑中,我们找到了伯格的一些旧笔记本。它们用特殊的速记符号书写,刻画精确,但即使对于我的德国土生土长的东道主来说,这些符号有时也让人颇为费解。当我翻阅其中一本页面发黄、书脊破裂的笔记本时,我发现了一些记录,这表明伯格还用了另一种方法来检验人的心理功能与物理和化学过程有相互作用的假设。根据热力学定律,能量所做的功总是伴随着温度的变化。伯格由此得出结论,即精神活动的变化(他称之为精神能量)也应该与大脑温度的变化相关。[3]伯格用细小的钢笔字在笔记本上画了草图,记下图表数据和注释。这是另一个实验的场景。
他的受试者还是医院的患者。这次是两名女孩,一个是12岁的癫痫患者,另一个是11岁的头痛症患者。外科医生在患者的颅骨上钻了一个洞后,伯格将直肠温度计插入女孩的大脑。根据铅笔画的解剖图来看,温度计插入的深度为21毫米。然后,伯格继续进行类似于体积描记的实验——给孩子施加各种感觉刺激,但这次是观察温度的变化。伯格1910年在专著《脑部温度的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emperatur des Gehirns)中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4]

图4 汉斯·伯格认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心理功能和情绪相关的精神能量变化应该伴随有温度的变化。为了检验这一理论,他把直肠温度计插入人和猴子的大脑中进行测量,并且记录下了大脑由于精神活动和感觉刺激而产生的温度变化
克里斯托夫·雷迪斯和我在精神病院的旧址附近找到了一处建筑,那里曾经是伯格的实验室。20世纪20年代初,伯格在这座附属建筑的地下室秘密工作,开始组装记录人脑电活动的设备。下班后,他独自工作,将精神病患者和自己的儿子作为实验对象。他的儿子克劳斯,就葬在我刚刚探访过的那座坟墓里。克劳斯后来也成为一名医生,但在1941年11月的战斗中阵亡,年仅29岁。
历史悠久的实验室大楼现在是一个小型图书馆。这里是人类第一次瞥见脑电波的地方。毋庸置疑,脑电波是近100年来电生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但这里却没有一块纪念牌匾。不过,图书管理员知道这座建筑的历史。他告诉我们,伯格的实验室就在地下室,但没有任何东西存留下来。图书管理员给我看了几张褪色的照片,上面是伯格摆满稀奇古怪的电子仪器的房间,还有头部连接着电线的第一批脑电图受试者,可惜伯格的所有设备都没有被保存下来。
伯格一直在用体积描记仪研究脑搏动,不过在研究脑电波的时候,他用其他设备取代了体积描记仪。在患者头部颅骨缺损的部位,他用镀锌的针头刺穿皮肤,让针头触及大脑表面。他将针头连接到仪器上以检测电流,但收集到的信号微弱且不稳定。对于他来说,很难区分检测到的信号究竟是代表流过大脑的电流,还是由于大脑搏动、心跳或肌肉的细微运动而引起的电噪声。他记录了部分患者大脑的信号,它们的波动似乎与患者的呼吸无关。这些患者包括一名40岁的男子。这名男子在5个月前刚做了切除脑瘤的手术,但伯格还是通过手术在颅骨上留下的孔把电极插入他的大脑。这名男子在伯格做完实验几周以后死亡,他的大脑出现了水肿,这让人们高度怀疑该男子是否为正常死亡。

图5 汉斯·伯格医生在精神病院工作期间做了关于脑电图的研究,他是第一个记录人类脑电图的人。他于1927—1938年担任德国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校长。在伯格的肖像下方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人类脑电图的论文中的一幅脑电图
又过了一段时间,伯格的仪器有了改进,技术也提高了很多。1924年的一个晚上,在同一栋楼内,他将两大片金属箔电极连接到12岁的儿子克劳斯身上,一个电极放置在后脑勺的头皮上,另一个电极放置在额头上,然后他把微弱的电信号输入一个被称为检流计的装置中。电信号转换为移动的光束,并在滚动通过设备的感光纸上记录下电压的波动。当克劳斯闭着眼睛坐着时,光束描绘出的脑电波图形是一种低频而缓慢的振荡。但是,当伯格要求克劳斯睁开眼睛时,克劳斯的脑电波突然变成一种不规则的高频率振动。伯格在患者、他的儿子甚至他本人身上进行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这些振荡的电波会因心理活动、觉醒、注意和感觉刺激等因素而改变,而且患有癫痫等疾病的人的脑电波形态会变得混乱。因此,这些脑电波不仅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大脑的运作机制,重新给出思维的定义,而且有助于医生诊断大脑疾病、判断智力水平和人格特质。但是汉斯·伯格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脑电波像无线电广播一样发挥更多作用。
二元论哲学认为,身心是相互独立且截然不同的。二元论者认为,我们的想法和情感等心理现象在本质上是非物质的,但是心灵、精神或思想与物理世界会有相互作用。对于当时的大多数科学二元论者而言,这只不过意味着身体刺激会产生精神活动,而头脑中的情绪或想法由大脑产生。然而,伯格将思维描述为一种力量——一种可以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精神能量”。他认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产生心理活动的精神能量改变时,必然会引起大脑中其他能量形式的改变,例如温度和电。他认为,在人脑中检测到的电波是精神能量和身体能量进行转换时产生的像涟漪一样的反射波。令人惊讶的是,伯格的发现证明,人脑的能量可以穿透颅骨进行传播,而且可以在远处被检测到。
在曾经是伯格实验室的这栋楼里,图书管理员检索到一部伯格于1940年出版的题为《灵魂》(Psyche)的专著。[5]伯格在扉页上用他特有的小体字题了词,但是除了每个句子开头的华丽大写字母外,其他文字潦草到几乎难以辨认,题词的最末更是变成了歪歪扭扭的细线。在这部专著中,伯格将心灵感应和精神能量联系在了一起。他描述了自己在1893年春季担任德国军队的志愿者时的经历,相信自己用心灵感应与姐姐进行了交流。在一次训练中,伯格的马突然直立起来,他摔到了地上。这时,一架马拉的炮车正好疾驰过来。幸亏驾车的炮兵及时刹住车,只是让年轻的伯格受到了惊吓,但没有受重伤。[6]就在同一时刻,伯格的姐姐在遥远的家中,突然强烈地感到他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她坚持要父亲立即给伯格发电报。这一事件给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战争结束后,伯格放弃了学习天文学的计划,转而投身医学。[7]多年以后,他在这部专著中写道:“这是一个自发的心灵感应的例子。在生命危在旦夕时,我想到了死亡。这种想法被传递了出去,而与我特别亲近的姐姐则充当了信息的接收者。”[8]
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伯格的研究也是游走在超自然心理学领域的边缘,因此,他被科学家同行们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的工作难以成为主流的原因之一。他发现在人的头上放置电极就可以接收从大脑放射出的电波,这证明了精神能量与大脑物质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作用。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的想法,但是,伯格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病院独立完成的工作颠覆了这一认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有可能直接监测人脑的认知和情绪状态。有了这一成就,人类通过脑电波远距离传播思想将不再是神话。

图6 汉斯·伯格首次用艾德曼扭弦检流计(Edelmann string galvanometer)在实施了颅骨环锯术(出于医疗目的而在颅骨上钻孔)以及颅骨受伤的患者头部记录脑电波。这些患者颅骨缺损的部位只覆盖薄薄的皮肤和疤痕组织。检流计中的扭弦通过透镜(2)聚焦到一卷溴化银相纸(4)上。相纸由皮带传动装置(1)卷起来,并显影形成照片。计时标记由音叉(7)产生。音叉以10赫兹的频率振动,由发条装置维持其振动。后来,人们在这套装置的扭弦上安装了一面小镜子,可以将光束反射到卷过的感光纸上
1924年,伯格在他位于耶拿的地下实验室中首次记录了人类的脑电波,但他没有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直到1929年,他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人类的脑电图》(“über das Elektrenkephalogramm des Menschen”)的论文,才算与世人分享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成果。[9]但当时很少有科学家注意到这一点。科学家们仍在使用还原论的方法:他们在显微镜下检查脑细胞;把不同的功能仔细地定位到某个大脑区域;研究单个神经细胞如何产生和传输电脉冲……人们在了解大脑的细胞基础和生理机制方面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伯格对大脑整体的活动进行记录的方法在当时顶尖的科学家看来没什么意义。他的工作看起来确实有点儿奇怪,因为大多数头皮电极记录到的电压波动是由肌肉活动产生的电干扰,而不是由大脑产生的脑电波。(当肌肉收缩时,它们产生的放电电压要比神经元产生的电压大得多;肌肉细胞比神经细胞大,而且位于连接传感器的皮肤下面,距离传感器更近。)
伯格发表的论文表明,他是最先发现人类脑电波的人,但他根本不愿意分享他的工作成果。他更多只是在保护,而不是促进这项研究。“好几个学期以来,我一直是他的助教,但我从没见他在课堂上提过自己的研究领域。”鲁道夫·莱姆克说。莱姆克于1931年加入精神病院,担任伯格的助理。[10] “直到1931年,在耶拿医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才知道伯格发表了一篇有关脑电图的论文。”莱姆克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听他演讲的同行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11]
但是,正如1931年1月4日刊登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篇报道所示,伯格石破天惊的发现并没有逃脱大众媒体的关注:
[汉斯·伯格测量到了!]他发明了一种仪器,可以记录大脑在精神活动过程中释放的电能。几年前,意大利神经学家费迪南多·卡扎马利博士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他用一种经特殊设计的无线电接收器来接收被认为是来自大脑的电波。这是“脑电波”的一个真实例子。但是,当卡扎马利要把这些“脑电波”和血流、心脏跳动、肌肉收缩等其他重要活动产生的脉冲区分开时,他遇到了困难。而伯格教授认为,他已经通过一种特殊的装置克服了这一难题。该装置使用附着在人体上的电极来接收所谓的大脑脉冲,而不是依靠伴生的无线电波。[12]
约翰·雷蒙德·斯迈西斯编辑过一本名叫《科学与超自然感知》(Science and ESP)的书,里面有一篇西里尔·伯特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介绍了费迪南多·卡扎马利做过的实验:记录一个大脑将信息直接传递给另一个大脑时产生的“电磁波”。伯特指出,伯格认为他发现的脑电波可能是心灵感应的方式,因此卡扎马利做了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脑电波传输的实验,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电磁辐射能产生这种传输效应的实验证据。因此,伯特得出结论:心灵感应的传播是通过精神能量的传递而发生的。[13]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对心灵感应和其他形式的超自然感知(例如透视和预感)的兴趣达到了巅峰。著名的普利策奖得主、《屠场》(The Jungle)一书的作者厄普顿·辛克莱就是超自然感知的坚定信徒。1930年,他自己出版了《心灵无线电》(Mental Radio)一书,详细介绍了他关于心灵感应的诸多实验,其中大部分是他与妻子合作完成的。无线电是“咆哮的20年代”的潮流。新兴的无线电技术和脑电波的结合迅速在社会上激起一阵狂热,但是就像1929年飙升后旋即崩溃的股市一样,这阵热潮也转眼间归于沉寂。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费迪南多·卡扎马利一直在罗马大学神经精神病诊所任职。与此同时,伯格在耶拿研究脑电波,但卡扎马利的研究重点是形而上学和心灵感应。卡扎马利不是把电极安装在头皮上,而是在一个人的头部附近放置一个无线电接收器来监视微弱的脑电波辐射。[14]卡扎马利在著名无线电工程师欧金尼奥·格莱塞塔的帮助下制造了复杂而精密的电子设备。卡扎马利投身于他的“心灵无线电”研究长达10年,并于1925年首次发表了他的发现。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是用意大利语发表的。[15]此外,还有一篇1935年用法语发表的论文。[16]因此,对于那些不懂这些语言或对超自然现象不感兴趣的主流科学家来说,卡扎马利的研究仍然晦涩难懂。
卡扎马利选择了他认为可能具有最强的心灵感应能力的人作为受试者——艺术家和音乐家。其中有一个受试者既是画家,也是登山爱好者。这个男人被领进一个陌生的房间,房间的墙壁上铺满了铅片,一只红色的灯泡发出诡异的微弱的光。铅墙对屏蔽人造无线电波和交流电产生的电磁干扰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微弱的脑电波辐射才有可能被检测到。
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一个金属架,上面装有电子放大器、整流器和一个频率被调到300兆赫的振荡器——这些就是无线电接收器的所有组件。墙边有一张沙发,画家被要求躺在上面并全身放松。卡扎马利将一个偶极天线放在距离画家头部约2.5英尺[17]的位置,信号会通过电线输入无线电接收器,然后胶片上就会记录下振荡器的输出。
卡扎马利请画家闭上眼睛,把脑袋放空。当画家保持放松的被动状态时,卡扎马利做了几分钟的记录。这位画家的登山经历不仅局限在意大利,他还到过安第斯山脉,也就是在那里发生过一场悲剧。正因如此,卡扎马利特意要求画家回忆他在巴塔哥尼亚的特罗纳多山遭遇的痛苦经历——在险象环生的山上寻找遇难同伴的尸体。此时,原先在记录胶片上绘出规则条纹的光束突然中断了,片刻后又恢复了之前的轨迹。卡扎马利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能让情绪激动的想法从受试者的大脑传播到了无线电接收器中,并中断了信号——这是心灵感应具有物理基础的有力证据。
在科学出版物数据库PubMed的所有记录中,你找不到任何文献引用过卡扎马利的研究。尽管神经科学家基本上都不认识卡扎马利,但在意大利,他却因为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而声名鹊起。1937年,费迪南多·卡扎马利与乔瓦尼·斯凯皮西和埃米利奥·塞尔瓦迪奥共同创立了意大利形而上学协会,以支持超自然现象的实验研究。[18]该协会一直维持到今天,并出版了《玄学:意大利超心理学杂志》(Metapsychic, the Italian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这本刊物。它由卡扎马利于1946年创刊,不公开出售,仅限于协会成员内部交流传阅。[19]
为了避免将这一段神秘的插曲视为历史的异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科学就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因此难免被真和伪的潮流裹挟,不时地陷入科学与伪科学纠缠的旋涡。2018年12月在博洛尼亚举行的意大利形而上学协会年度会议上,威廉·吉罗尔迪尼是发言人之一,他介绍了关于心灵感应和脑电图的研究。[20]
科学研究被庸俗化及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能会让科学界内部的人对科研成果本身的看法产生扭曲。这样的教训古已有之,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什么改观。1930年7月,在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用更加狂热和浮夸的语句向公众吹捧伯格的发现:“今天,大脑书写的信号对我们来说还是神秘的;明天,我们可能就可以解读神经系统病变和精神疾病;后天,我们就要开始用脑电波写生平第一封诚实的信了。”[21]
达成这样的成就一直是人类一个不灭的梦想。当我在2019年撰写本书时,有报道称脸书的创始人、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和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正在投资一些项目,它们旨在从人的脑电波中提取思想和情感,并将其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然后直接下载到其他人的大脑,让人们实现单靠意念就可以操纵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梦想。[22]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拜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他们也在利用脑电波来研究“读心术”和“心灵感应”这类交流方式。这样你就可以进行对比,看看大众媒体上的报道和它们背后的现实。与伯格所处的时代相比,这个话题现在已经不那么容易引起轰动了。
1929—1938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伯格每年发表一篇或多篇关于脑电波研究的论文,但全部14篇论文的标题都是一个——《人类脑电图》,并且都发表在同一刊物——《精神疾病与神经疾病案例》(Archiv. für Psychiat. Nervenkr)上。这种特殊的做法进一步掩盖了他的实验结果。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标题通常会对所要报道的新发现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但是在伯格这一系列论文的标题中,人们找不到有关他的实验发现的任何线索。任何科学家如果对伯格在实验中发现的东西感兴趣,都必须仔细研究这14篇标题相同的论文,就好像要找一份隐藏在不是3扇,而是14扇相同的门背后的奖品一样。伯格的这些论文也很难被引用,因为这14篇论文仅在出版年份上有所不同。他用这种方式掩盖他的发现,将它们隐藏在主流科学界的视线之外,并尽量减少这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
自1924年首次记录人类脑电图以来,伯格的工作几乎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34年,诺贝尔奖得主埃德加·道格拉斯·阿德里安注意到脑电活动现象,并且在他与布赖恩·哈罗德·卡伯特·马修斯合著的论文中重复了伯格的实验。这篇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大脑》(Brain)上。[23]在那篇论文中,阿德里安和马修斯含蓄地嘲讽了他们所谓的“伯格波”的重要性,其中有一张图把阿德里安在睁眼和闭眼时脑电图的变化与龙虱在有光照和黑暗条件下产生的电波变化进行了比较——结果龙虱产生的电波与诺贝尔奖得主产生的脑电波相同。[24]此后,阿德里安没有继续从事脑电图的研究,整个医学领域对伯格记录脑电图的兴趣仍然不大。
“伯格每年在耶拿医学学会上都会发表有关他研究的演讲,但并没有得到几个人的赏识。”鲁道夫·莱姆克说,“1934年,在德国明斯特市召开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会议上,伯格做了关于脑电图的报告,也没有引起他所期望的反响。”[25]神经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玛丽·布拉齐尔在她1961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脑部电活动的历史:第一个五十年》的最后一行中写道:“伯格(对人类大脑电活动的研究)在头50年里所做的贡献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就是成功记录了人的脑电图。”[26]
离开伯格做出重大发现的地方之后,我跟随克里斯托夫·雷迪斯来到校园里另一个图书馆的地下室。该图书馆刚刚收到了汉斯·伯格的一位前同事的捐赠,捐赠物品包括他保存下来的伯格的信件、照片和便笺,这些物品还没有被图书馆登记入册。我拿起一张照片,上面是人类最早的脑电图的真实记录,这正是近一个世纪前汉斯·伯格手里拿着的那份记录。
伯格在这家精神病院几乎与世隔绝地工作了近30年。这家医院距离他的墓地仅几步之遥。伯格看起来并不像是那种能够取得重大科学突破的人。为什么当时没有其他人从事这一研究呢?[27]是什么促使伯格做了那些奇怪的实验,并让他走上了发现脑电波的道路?
为了追溯伯格的灵感来源,我要去意大利都灵的山区。19世纪80年代,即伯格进行实验的近20年前,安杰洛·莫索第一个记录了人脑活动。但是,莫索记录的不是大脑的电活动。他开发了后来伯格所使用的体积描记法,并用它来监测大脑中的血流如何因劳累、呼吸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为适应都灵周围山区的高海拔环境而发生变化。伯格关于脑容量变化的早期研究直接借鉴了莫索的研究和方法,伯格在1901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中高度赞扬了莫索。[28]现在的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就是利用大脑局部区域的血流变化来定位某些神经活动发生的位置。它的起源也可以直接追溯到安杰洛·莫索,而莫索只能使用19世纪科学家的原始方法进行类似的研究。
我去莫索位于都灵的实验室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
肿胀的大脑
在意大利阿拉西奥一个沿海的村庄,我为了躲避冰冷的雨水而逃进了罗姆咖啡屋,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在这家咖啡屋的墙上潦草地写下他的名字。在墙上留名这个具有传染性的习俗让我无法抗拒。前一天,我去西班牙萨拉戈萨的一家医院。当我滑入fMRI设备的扫描舱,看着机房天花板消失时,几周前母亲的责骂声又在我的脑海中回荡:“为什么要弄坏你的脑子?你的脑子好得很。”
这是个好问题。
当我读到两位西班牙研究人员——放射科医生尼古拉斯·费耶德博士和神经学家佩德罗·莫德雷戈博士——的论文时,一切就开始了。[29]在对一个珠穆朗玛峰登山探险队的13名队员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返回的队员除了一个人外,其他所有人都有物理性脑损伤,这在fMRI检查时清晰可见,就像在X射线下看到的骨折一样。这些损害是永久性的。

图7 安杰洛·莫索(1846—1910),意大利科学家,最早使用仪器进行脑功能定量研究的人之一。他使用体积描记法测量颅骨缺损患者的脑容量波动,这给汉斯·伯格的研究带来了启发。莫索特别感兴趣的研究是高海拔对大脑有什么影响。他在意大利都灵的罗莎峰建立了实验室,以进行这项研究
登山者都很清楚,高海拔地区的稀薄空气会造成所谓的高原脑水肿(HACE),从而引起严重的疾病。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会导致大脑损伤和死亡。人体对缺氧的反应会增加毛细血管内部的压力,导致液体渗到周围的脑组织中,使大脑肿胀并造成灰质被颅骨压迫,从而对性命构成威胁。这正是安杰洛·莫索所研究的现象,并且在未来它将给伯格的工作带来启发。莫索将他的压力测量装置安装在颅骨缺损的人的头上,在他们攀登罗莎峰到达15 000英尺时(莫索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顶实验室,研究高原反应和适应高海拔条件的生理机制),对他们大脑水肿的程度进行了监测。
海拔对某些资深登山者的认知能力会产生持续的影响,这在登山者中是广为人知的——他们通常用“嗨”来形容这种感受——但大多数攀登高海拔山峰的登山者认为,如果一个人能正确地自我调适,就可以避免严重的高原反应和脑损伤。实际上,有关高原反应最早的报道来自僧侣,他们跟随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纪深入安第斯山脉。机敏的僧侣们注意到,将军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但他们手下的士兵却安然无恙。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因为将军骑马很快就登上了山峰,而士兵们徒步攀登,速度慢得多。(除了服侍上帝,僧侣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酿酒大师;他们的所有活动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登山的速度要慢,因为身体适应的过程很缓慢。身体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适应高海拔处的低氧环境,这涉及一系列神奇而复杂的生理变化。周末的勇士们不但付钱给导游,让他把包扛到山顶,还为自己因缺乏耐心而导致的严重疾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适应是需要时间的。虽然费耶德和莫德雷戈的论文中的受试者对高海拔的反应比较温和——只是出现头痛、恶心、疲劳这些几乎所有登山者都能忍受的症状,没有人出现更严重的症状——但这些都是高原脑水肿的标志。简而言之,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大脑受到了伤害,更不用说永久伤害了。西班牙研究人员随后研究了那些攀登较低海拔山峰(比如颇受欢迎的阿空加瓜山、乞力马扎罗山和勃朗峰)的登山者。尽管这些攀登较低海拔山峰的登山者中出现脑损伤的概率较低,但还是在一些登山者的脑部MRI(磁共振成像)检查中发现了同样的损害。同样,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出现高原脑水肿症状,但是,他们的大脑在高海拔条件下肿胀的程度足以造成伤害。
作为神经科学家,同时也是登山爱好者,我发现费耶德和莫德雷戈的论文特别有意思。我意识到,对于那些关注登山对大脑有什么影响的普通读者而言,在这个主题上可以大做文章。我与《户外》杂志的一位编辑接触,并提出要亲自去攀登“美国的勃朗峰”——雷尼尔山。当然我会格外小心,让自己先适应环境,并在登山前后都进行MRI检查,以证明登山是安全的。他们很喜欢这个提议,于是跟我约了稿。[30]
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没有科研机构愿意跟我合作,给我做大脑MRI检查,哪怕我自己掏钱去医院或者是到大学的实验室去做。仅仅因为研究某种损伤的课题很有意思,就要把一个人置于可能受伤害的环境,很显然,这样做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我的计划陷入了停滞。后来,我忽然想到应该与费耶德博士联系。最初,就是他对登山者的大脑进行了研究。“没问题!”他同意了,“诊所下班后,你就可以过来,等我们为您做完MRI检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这就是我决定要做的。我没有“以前”的MRI图像,但是至少我会看到多年的登山经历是否损害了我的大脑。在去萨拉戈萨的路上,我要顺道去意大利都灵,看看安杰洛·莫索进行脑肿胀研究的实验室,那是汉斯·伯格的灵感来源。不过,首先我要去爬山。
登上雷尼尔山
我和我的登山搭档、我儿子迪伦会合了。每一个登山季都会有数百名业余登山者尝试征服雷尼尔山,因此,它是调查高海拔疾病的理想之地。雷尼尔山坐落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是一座被冰川覆盖的活火山,从海平面陡然上升到海拔14 410英尺。大多数登山者从这里开始攀登。像勃朗峰一样,人们经常选择在周末去尝试攀登雷尼尔山,但周末的时间太短,无法让身体在高海拔地带充分适应稀薄的空气。不过,迪伦和我会多花点儿时间做前期的适应准备。
登山季节已经结束,在雷尼尔山上的登山队和大多数其他登山者已经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做好了准备。即使有可能出现雪盲,迪伦和我还是决定在帐篷里等待恶劣天气过去,风暴一过就准备登顶。我带了脉搏血氧仪来监测我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在攀登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特别难熬,我的血氧饱和度迅速降至75%,而心率飙升至每分钟165次。(提高心率是人体为了弥补氧气供应减少的生理机制之一。)我见过自己的血氧饱和度降到过更低的水平,那是在攀登厄瓜多尔海拔19 347英尺的科托帕希峰时。还有记载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的血氧饱和度甚至会降到50%左右。在正常海拔下,可能只有在重症监护病房才能看见人的血氧饱和度那么低,并且从医学角度来看,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于90%,就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在高海拔地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与氧气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变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变化)使我们的需氧量减少了。这证明,如果适应时间足够长,人体自身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当然,所有的生理指标都无法排除登山带来的某些风险。在下山的路上,我的冰爪在冰冻的山坡上被绊了一下,于是我头朝下摔了下去。当你听到某个登山者丧生的消息时,通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尖叫着从冰冷的斜坡上滑下来,接着飞过悬崖,坠入裂谷间的深渊(我讨厌裂谷),或者被一块突出的岩石挡住,就像砸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虫子一样被摔成肉泥。我跌跌撞撞地从山峰上摔了下来,知道自己唯一的逃生机会是将冰斧凿入地面,阻止身体呈指数级加速下滑(科学家都知道这个加速度是32英尺/秒2)。一旦速度太快,你将无能为力——你的斧头会从冰面滑过,如果达到每小时60英里[31]的速度,冰面将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坚不可摧,而你的搭档只能眼看着你掉下去……就是这样。除非像迪伦和我当时那样拴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伙伴还可以尝试用自己的斧头来固定住绳子的另一端,然后把你猛地拽住……不过,一旦失败,他将和你一起摔死。我在不断加速下滑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这种状况,于是,我迅速弓身一挺,把自己调整到适当的位置(头部朝上),使劲地朝山坡挥了一下冰斧。我的冰斧劈进了冰面。我用左手抓住斧头,用右肩猛撞,将斧刃推入冰雪中,在山上拖出一条沟。我下滑的速度慢了下来,最后终于在撞到迪伦之前停了下来。而他已经摆好姿势,像保罗·班扬一样举起斧子做好挽救我们两个人的准备了。
这是一段难忘的回忆——缺氧难受,坠崖更糟糕。
回到西雅图的海滨,富含氧气的空气像奶油一样浓稠,我感觉自己可以像蛙人一样在里面游泳。由于我的身体在山间稀薄的空气中是超负荷运转的,现在一切回归正常,我感觉自己像超人一样有无穷的体力和精力。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几天,却令人印象深刻。不难看出,住在都灵的群山之中的莫索为什么会心动要去研究海拔的影响了。
登山结束后,我去了意大利,看看莫索工作的地方……然后去西班牙检查我的脑袋。
登山者的大脑
詹尼·洛萨诺博士在生理研究所(Instituto de Fisiologia Umana)外面等我,那是都灵大学的一幢建于19世纪的石头建筑。洛萨诺是一个温柔的男人,当时就在安杰洛·莫索曾经用过的办公桌上工作。巨大的橡木桌子和皮革座椅摆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中央。办公室的拱形天花板足足有20英尺高,地上铺的是拼花木地板。今天是星期六,大楼里空无一人。洛萨诺带我去见他的同事达里奥·坎蒂诺,后者是研究莫索的专家,专门把莫索的著作由意大利语翻译成英语,并在互联网上发布。
坎蒂诺本人既是科学家又是登山者,是一个瘦小精干的男人,有着旺盛的精力和开朗的性格。他还是个挑剔的科学机械仪器收藏家。他带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参观:其中一个房间里是他收藏的电子显微镜——从20世纪50年代最早的设备(类似于鲍里斯·卡洛夫的老电影中的东西),到最新的模型。另一个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印刷机,盒子里堆满了配套的铅字。坎蒂诺收藏的印刷机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都没有地方存放了,有些只好放在户外,用篷布遮盖,以免受到侵蚀。
“为什么要收藏印刷机?”我问他。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坎蒂诺想了足足有一分钟,他说也许是因为印刷机记录并翻译了信息和思想。这正是他本人所做的工作——既作为一位科学家将数据转化为见解,又作为一位译者将莫索的著作翻译成英语。坎蒂诺走到一台巨大的印刷机旁,挑选了一个有我手掌大小的铅字,送给我留作纪念:一个“?”。这是一位科学家送给另一位科学家最好的礼物了。(我妈一定会觉得,将其作为我目前工作的标志性符号也挺合适)。
接下来,洛萨诺和坎蒂诺带我去图书馆。在那里,安杰洛·莫索的笔记本和仪器被井井有条地分类摆放在一个仅对学者开放的房间内。涂了炭黑的记录鼓由黄铜发条装置带动旋转,测量血压和脑容量变化的装置摆放在桌子上或存放在展柜里。有一些照片记录了受试者在做脑容量测量时的样子,还有一些照片记录了莫索做的其他各种高海拔对人体影响的实验。当我拿起一张发黑的纸条时,我的手指上弄上了一层淡淡的炭黑。纸条上描绘了精细的振荡痕迹,这些痕迹是人类大脑活动最早的记录之一。我心里明白,我现在有幸触摸到了这样两份前所未有的历史记录(一份是监测血流的记录,另一份是监测电信号的记录),每一份记录上都留有一个世纪前创造它们的科学家的指纹。
我从都灵出发,开了几乎一天一夜的车才到达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其间我想绕道去瑞士,但是却在法国某个地方转弯时走错了路。萨拉戈萨健康保健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尼古拉斯·费耶德博士个子很高,头发灰白,态度随和友善,还挺有幽默感。他的同事海梅·梅德拉诺博士在我们交流时给我们当翻译。费耶德问了我登山的情况,然后笑着说:“要想成为一名登山者,必须要有一点点疯狂。”这意味着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

图8 安杰洛·莫索用于研究高海拔对大脑和身体影响的仪器。体积描记仪有一个缓慢旋转的滚筒,上面是涂过炭黑的纸。仪器检测脑容量波动时,会用一支笔把纸上的炭黑刮下来进行记录
MRI控制室旁边就是费耶德博士的办公室。我们走了进去,他取出一些资料,桌子很快就被登山者的大脑扫描图像铺满了。
他指着黑白胶片上的一张大脑断层图说:“额叶萎缩。”前额的后面就是前脑的位置,在那张扫描图像中,它像干果一样枯萎了。这是在前额叶切除术中被切断的大脑区域。做了这种手术的患者智力没有受损,但某些高级执行功能,如注意力和计划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空间感”——出现了缺陷。我曾带着对临床的兴趣,在已发表的论文中仔细研究过类似的图像,但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每一幅图像上都标有一个登山者的名字。

图9 作者手上拿的是安杰洛·莫索使用体积描记仪做的一份生理反应记录
“何塞遭受了最严重的伤害。”费耶德说。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健壮男子,站在阿空加瓜山白雪皑皑的山坡上,他的黑发随风飞扬,胡须浓密,皮肤被高海拔的太阳晒成了古铜色。他看起来健康又坚毅,是我很乐意交往的那种人。费耶德接着说:“当何塞回来时,他不记得自己的电话号码了。他的妻子要他去商店买一条面包,他居然忘记他为什么去商店,然后空着手就回家了。”
“看到前脑的病变了吗?”费耶德指着另一张扫描的片子问我。这类病变是由于脑部小范围的卒中或出血引起的。它们在登山者的整个大脑中都有分布,表现为MRI上的亮点,但在白质区域尤其常见。白质就像棒球的核心一样,由数百万条紧密连接的神经束组成,这些神经束将大脑表层的神经元连接成网络。大脑中任何地方的白质损伤都可能造成严重而广泛的后果,就像挖掘机挖断1码[32]长的电缆就可以造成整个城市大面积停电一样。白质似乎特别容易发生缺氧,因为它的毛细血管供应很少。
11名登山者的脑部MRI结果都显示他们的菲-罗间隙(Virchow Robin Space,脑部血管与周围脑组织之间的空隙)扩大了,这是由于脑部肿胀和脑组织缺失造成的。不一定非得医学院毕业的人才能看懂这些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散布在大脑深处的白色霰弹枪眼。菲-罗间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结构,随着我们大脑的衰老,这些空腔也在扩大。虽然老年人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普遍存在多个菲-罗间隙或菲-罗间隙显著增大,但是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岁(也就是这些登山者的年龄)的健康人身上并不常见。
后来,我在MRI控制室遇到了科拉尔·罗娅。令我吃惊的是,她告诉我说自己是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海拔19 340英尺)的受试者之一。所有7名登山者都出现了典型的轻度高山病症状,但是没有人发生高原脑水肿或其他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在登山之前进行了MRI检查,都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在返回后,其中一个人的大脑菲-罗间隙扩张了。在参加攀登勃朗峰(海拔15 781英尺)测试的另外7名业余登山者中,其中一人回来后出现了皮质下病变,另有两人脑部出现多个扩张的菲-罗间隙。
这些参与实验的登山者大多是医生和工程师。我问费耶德,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看到自己大脑受损后停止了攀登。“他们都还在攀登。”费耶德告诉我。
“我们的目的不是阻止人们去攀登,”莫德雷戈博士强调,“而是想让人们意识到危险,并且做好适应环境的准备。”
现在轮到我了——揭晓的时刻。我脱到只剩内裤,穿上绿色的纸靴子和浅蓝色的医用罩袍。这身装束让我立刻感到脚瘫手软。
助手伊丽莎白·佩雷斯微笑着递给我一对柔软的粉红色耳塞,让我在做检查的时候塞进耳朵,以阻挡MRI机器扫描时产生的噪声。一条狭长的检查台从一台像工业干衣机的巨大机器里伸出来,我像法老的木乃伊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上面。她根据照射到我头上的光网调整我头部的位置。接着,她将一个看起来像棒球捕手面罩的东西拉到我的脸上,然后启动机器,将我头朝前地送入扫描舱。如果这是詹姆斯·邦德的电影,那么现在就应该亮出Q博士的发明,搂住佩雷斯女士的腰,然后和她一起逃出生天……但是我勇敢地将幽闭恐惧症压制住了,尽量不动肌肉,不然会使照片模糊。
检查开始了。即使用了耳塞,我还是觉得震耳欲聋,听起来就像在我的颅骨内施工——锤子和电锯的声响中间穿插着奇异的电子游戏的音效。我忽然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把我的大脑像切薄火腿片那样一层一层进行扫描时到底会看到什么?登山留下的伤疤根本不算什么——如果他们发现我有致命的脑瘤怎么办?霍默·辛普森的头部X射线图像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脑壳里只剩下一个核桃大的脑子,这让我心神不宁。
通过挂在我眼睛上方的镜子,我可以从两只绿色靴子之间看到医生和技术人员。很少有人愿意把头伸到机器里,因为从我这个角度来看,这台机器就像个断头台,所以,镜子的作用是减轻患者的压力。他们聚在玻璃窗后面,盯着计算机屏幕上的扫描结果,但是我没有戴眼镜,无法分辨他们究竟是看到了什么令人困惑的东西,还是看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正在拿它开玩笑呢。
检查结束后,我焦急地走向围着计算机屏幕的那群人,他们可比把我送进扫描舱的医生热心多了。屏幕上正在显示我的检查结果。
费耶德博士说:“完全正常。”他和梅德拉诺博士快速浏览着屏幕上的图像。这些断层图像从头部一侧开始,一层层进入皱褶的大脑皮质,然后抵达大脑的核心部分,最后从头部的另一侧穿出来。而与此同时,我真正的大脑正高速运转,试图完全理解这些图像。费耶德博士停下来,指着一张图像说:“一个很小的菲-罗间隙。”他上下拖动看了看,然后说:“还有一个。”
“完全正常,”莫德雷戈博士向我保证,“与您的年龄相符。”
见鬼!这意味着什么?
费耶德博士将我大脑的3D图像刻录到CD上,然后微笑着递给我,仿佛递给我一副算命用的塔罗牌。
纳粹和脑电波
汉斯·伯格是自杀身亡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位非常熟悉供血不足对大脑的致命影响的科学家来说,他选择了上吊。
伯格1919—1938年一直担任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后来,他被授予名誉教授并退休。退休后,他在新主管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直到1941年去世。鲁道夫·莱姆克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教授,也是伯格的助手,他协助伯格记录脑电图。莱姆克在1956年写了一篇纪念汉斯·伯格的文章,发表在一份专门研究脑电图的科学期刊上。[33]“伯格不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因此他不得不离开他所供职的大学。”他写道,“没想到,这让他深受其害。”
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凡是不与纳粹结盟的各界领袖都遭到了清洗。伯格是残暴的纳粹政权的又一牺牲者。他在耶拿医院里上吊自杀,用的是电线(这真是又一个讽刺)。人们认为,伯格自杀是为了表达他对纳粹的反抗,或者是纳粹对他的报复使他彻底绝望。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界得到了回应和强化。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癫痫和脑电图专家伊莱·戈尔登松博士写道:“伯格表现出对政权的不满,他们对他进行了报复。1938年,他被纳粹官员羞辱,他们突然将他解职。”[34] 2005年,该领域的另一位开拓者恩斯特·尼德迈耶写道:“伯格与纳粹政权的关系不好,他被授予名誉教授,这让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突兀。”[35]
众所周知,纳粹恐怖的“最终解决方案”最早就是用在精神病院。“种族卫生”的概念包括清除社会中所谓的“劣等人”,因为这些人不利于保持基因的纯洁性,所以要么阻止这些人繁衍后代,要么直接消灭他们。精神病院在20世纪早期这场优生学的疯狂中冲在最前面。早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前,强迫有精神疾病或身体残疾的人绝育已是当时精神病院里的普遍做法。希特勒的首个灭绝方案就是对精神病人实施安乐死。纳粹分子使用的杀戮方法和工具(包括毒气室),是在德国的精神病院开发出来的,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后来被用到死亡集中营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优生运动和种族卫生政策标志着纳粹主义的兴起,而伯格此时担任精神病院的负责人,正好处在风暴的中心。
战争结束后,耶拿被苏联接管,但战争期间在大学和医院中的许多负责人战后仍在担任要职。这种情况妨碍了苏联调查前纳粹分子或保存资料,导致真相被掩盖。由于许多记录丢失或毁坏,那些幸存者撰写的历史往往是一种混杂了当时的伤感情绪的叙述。正如我访问耶拿时遇到历史学家苏珊·齐默尔曼时发现的那样,这种叙述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
伯格的同事鲁道夫·莱姆克实际上是纳粹党成员,不过他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认为伯格是反对纳粹的。莱姆克是纳粹党的成员,从遗传健康法庭(Erbgesundheitsgericht)成立之初就在那里工作。1934年1月1日,德意志帝国设立了遗传健康法庭,对精神和身体不健全的人进行强制绝育。“不健全”这一定义非常广泛,它包括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和酗酒者等。[36]到1945年5月,约有35万人通过遗传健康法庭被强制绝育。[37]战后,莱姆克留在耶拿,他的活动以及他反犹太人和反同性恋的恶毒观点被当局掩盖了起来。1945—1948年,莱姆克成为精神病院的负责人。他荣耀的学术生涯一直持续到他1957年去世,即他发表为汉斯·伯格进行粉饰的回忆录的第二年。
伯格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种族清洗、安乐死和强制绝育的暴行做何感想呢?齐默尔曼向我展示了伯格的笔记本中的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抱怨说,希登塞岛是波罗的海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现在岛上的犹太人太多了,已不再适合度假胜地的美名。这些是他的个人笔记,由此可以大致推想出他的真实情感,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自己的实验笔记本中写下这样的反犹主义评论呢?是不是他正在拿一个犹太教徒做实验?我们不知道。但是带着种族主义的嘲讽就摆在那儿,是他亲手写的。
齐默尔曼告诉我:“伯格是1934年党卫军的支持者。”“支持者”本身不是党卫军成员,但他们通常会以经济贡献来换取成员资格。“许多人想成为党卫军成员,以图在职业上得到升迁。”齐默尔曼解释道,“伯格是不是纳粹党的成员还未可知,他有可能不是这个纳粹核心组织的成员,但当时有许多小型纳粹组织。纳粹团体并非只有一个。”
齐默尔曼抽出一沓她从民主德国的斯塔西(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构)警察那里获得的档案。她递给我一份法院诉讼程序的官方文件。这份文件记录了伯格参加过那些因被要求绝育而提出上诉的人的听证会。其中包括一名18岁的智障人士、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一名癫痫患者、一名61岁的酗酒者和一名智力和记忆力均低下的妇女。这名妇女在丈夫的陪同下出席听证会,她的丈夫恳求法院不要对他的妻子实施绝育手术。伯格否决了所有上诉,判处他们所有人强制绝育。
我问:“他有没有可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被迫服从纳粹?”
“不可能。”齐默尔曼回答道。伯格于1938—1939年在上述法庭的健康与遗传疾病(强制绝育)部门任职。“那是他退休以后发生的事。”她说,“那个时候,他不再有与纳粹或绝育组织合作的职业上的动机。”
伯格与另一个纳粹党成员卡尔·阿斯特尔也过从甚密。阿斯特尔因追求所谓“种族纯洁”的所作所为而声名狼藉。阿斯特尔于1939年成为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校长,并努力将该大学塑造为党卫军机构的典范。他还是纳粹“健康事务部”的负责人和“种族卫生研究所”所长。1941年3月4日,伯格应阿斯特尔的邀请,继续从事在医院监督强制绝育的工作,并写道:“我很乐意再次担任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顾问,对此我深表感激。”但是伯格生病了,无法工作,仅两个月后,他自杀身亡。伯格患有慢性抑郁症,他感觉身体不适,后来在医院里做检查时自杀。齐默尔曼说:“尸检没有发现伯格有患病的迹象。”1945年4月3日,卡尔·阿斯特尔也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多跟纳粹同流合污并在战争结束时才发现自己是失败者的人都是这个结局。
在我结束与齐默尔曼的交谈后,克里斯托夫·雷迪斯带我去了大学的解剖系,该系因其收藏的标本而著名。他打开门,然后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整齐地摆满了装着人体解剖标本的瓶瓶罐罐和陈列着人体骨骼的玻璃柜子。我惊奇地看到了各种各样被肢解的人体器官标本:女性生殖器官、剥了皮的勃起的阴茎、睾丸,以及从婴儿、儿童到成人的骨骼。房间里有很多装着胎儿的罐子,有些胎儿有严重的先天畸形,其中有一个双头的胎儿;还有头部被切开后各个部分的标本;有四肢、手掌、手臂和腿的标本,被剥去皮肤,露出肌肉和骨骼。
这些标本都是无价之宝,是人体解剖教学的重要辅助工具。我们需要为科学家和医生提供有关人体解剖学的培训,只有对人体有所了解,人们才能获得药物治疗和缓解痛苦的方法。不过,很难想象那些为了科学而将尸体捐献出来的人竟然那么慷慨,明明知道医学生会把他们切开,还愿意在死后让他们的肉体被肢解:每一根手指、每一个器官被一点一点地分割;他们的脸皮被剥去;为了展示大脑,他们的头被切成像火腿片一样的薄片;他们的生殖器被切开检查。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以保留其在生前的样子,虽然这对于埋在黑暗的地下6英尺深的尸体来说毫无意义。然而,那些愿意将尸体献给解剖学家和医学生的人知道,他们的尸体完全是无用的,只不过是虫子的食物。他们尊重肉体存在的意义,它是一个存放灵魂的神圣的容器。他们献出尸体以挽救其他生命,训练医师,并让科学家深入了解人体这台奇妙的机器。他们是勇敢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命和健康都应该归功于他们。
在我拜访期间,雷迪斯和齐默尔曼在刚刚发表的科学论文中说,他们发现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收藏的解剖标本中有大约203具尸体来自1933—1945年被纳粹处决的囚犯;其他200具尸体是精神病院和养老院中被实施安乐死的患者;另有数十具尸体是在强制劳改营中死亡的人。[38]
“当时有人支持医院实施安乐死,因为解剖学家需要标本,他们欢迎这种尸体来源。”齐默尔曼说,“这也解决了纳粹处置尸体的问题。”
将人类的大脑捧在手中并进行解剖,我敢说任何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总会想到死去的这个人。这是对一个人无私地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科学时应有的神圣、庄严和感激之情。但如果所展示的解剖标本是来自一场谋杀的受害者,那么这件事就不是因不敬而让人感到厌恶那么简单了,它是人性的堕落。任何体面的科学家或医生都不会愿意参与其中的。雷迪斯和齐默尔曼揭开真相以后,所有被鉴定为来自劳改营的死者标本均从解剖展览室中被移除了,大楼外还悬挂了一块牌匾,以向这些死难者表达敬意。但是,由于解剖工作的性质,许多身体部位的标本已无法追查到来源。于是,这些珍贵的藏品笼罩了一层永远都无法褪去的阴影。
同样,伯格的遗产也蒙上了一层灰色调。汉斯·伯格到底应该被认作领先那个时代一个世纪,努力尝试用原始设备来铸就知识上的伟大成就的拓荒者,还是为了解开精神和肉体的分界这个亘古之谜而不惜采用怪异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方式和使用简单的设备(例如压力计、温度计和检流计)的科学怪人?
“他是天才还是疯子?”结束耶拿之旅时,我问一小群学者。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回答我:“他疯了。”其他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怎么能将直肠温度计插入年轻女孩的大脑呢?[39]他怎么能在病人苦苦哀求的情况下,还坚持判处他们强制绝育呢?漠视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权并非伯格或德国所独有,但无论发生在哪里,这种事情都是暴行。无论历史如何书写,伯格本质上就是个纳粹分子。但他也做出了重大发现,人类世世代代都因他的发现而获益,并能从中不断获得启发。这两个伯格都是真实的。
伯格和贝克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伯格决定探索大脑中的电活动是天才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自18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信号可以通过生物电在神经系统中传输。不过,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以及电本身的性质在当时还是个谜,更不用说诸如思想之类的心理功能可以形成穿透人类颅骨的电活动波——而且是普普通通的可被识别的电波——的想法了。但是,伯格并不是第一个使用电极连接到电子仪器来探索大脑可能产生电能的人。实际上,就像他重复莫索监测血流的方法一样,伯格只是重复了别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一个人。
希特勒的黑名单
在许多方面,波兰科学家阿道夫·贝克与伯格正好相反。这两个男人都受相同的好奇心和激情驱使,也都被同一个邪恶的政权吞噬,但他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是帮凶,另一个是受害者。这两位科学家的命运因纳粹狂热的战争暴行而纠缠在一起,并因灵感而相互联系:贝克在波兰的工作启发了伯格在耶拿的秘密研究——探索人类大脑通过产生电磁能来运作的可能性。
19世纪80年代,脑科学家们专注于确定大脑的哪些部分执行特定的功能。第一种实验方法是切除实验动物脑组织的特定部位,并观察结果。这种方法在20世纪初就已被广泛应用。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方法很有用。例如,人们发现一侧大脑半球某些区域的皮质损伤会导致身体另一侧瘫痪,从而找到运动功能的定位,但有时这种方法无法提供任何线索。例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就训练大鼠跑迷宫,然后系统地切除它们的一部分大脑,并让大鼠再次执行跑迷宫的任务,目的是探明记忆的存储位置。拉什利发现,大脑皮质的什么部位被切除似乎并不重要。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他最终放弃并承认失败。他于1950年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在大脑的任何地方给“记忆痕迹”进行定位。[40]如今,我们在如何对心理功能进行大脑定位的方向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并且知道,“寻找特定心理功能在大脑中的定位”这个根本假设是错误的。尽管大脑的某些位置确实与具有特定功能的神经元群体相对应(例如,大脑的背侧与视觉功能相关,大脑皮质的布罗卡区与语言表达功能相关),但许多心理功能的完成,需要在大部分脑区的神经网络间进行广泛的信息传递。尽管如此,探索与特定的心理、运动或感觉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和大脑回路这项工作依然非常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而且对于治疗颅脑损伤和进行神经外科手术也是必要的。

图10 波兰科学家阿道夫·贝克(1863—1942),他在189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记录了放置在实验动物裸露的大脑和脊髓上的电极所产生的脑电波。贝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国人囚禁了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要把贝克带到亚诺夫斯卡集中营,当时贝克就快要过80岁生日了。他吞下一颗氰化钾胶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世纪80年代,通过简单地破坏一部分大脑皮质来定位控制运动功能区的实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要确定感觉信息在哪里进行处理的问题却复杂得多。人们很早就知道,神经是通过电脉冲来传递信息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用于记录电信号的设备也为确定传递感觉信息的神经回路提供了一种新技术:在大脑的某个点上放置一个记录电极,来检测对感觉刺激的反应,就像电工用电压表探测电子设备的电路一样。
但是,相比电工使用电压表,19世纪后期的神经科学家所做的事情要困难得多。要知道,对神经系统电活动的所有开创性研究都远远早于电子放大器以及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发明。这些实验是在用煤气灯和蜡烛照明的房间里进行的。那时人们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是马车,更谈不上了解电的基本性质了。请想象一下,没有电气设备,只能用简陋的装置和厨房里可以找到的东西来记录实验动物大脑的电反应,你会怎么做?
当时,用于检测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电现象的最灵敏的仪器是弦线检流计。在弦线检流计中,一根磁化的针被一根细线悬在两个线圈之间。当电压通过电路时,针周围的电场会受到干扰,使指针略微偏转,就像指南针在靠近金属物体时那样。由于神经系统的电活动非常微弱,指针的偏转角度非常小,所以需要借助放大镜进行观察;但是,就像在演示PPT时使用激光笔,手的轻微颤动会被激光笔放大一样,如果把一面小镜子固定在细线上并用一束光照射小镜子,那么指针的偏转就可以等同于镜子的反射光的偏转;这样一来,指针的偏转就可以被放大了。镜子将光束反射到一个刻度尺上,我们在刻度尺上可以容易地测量出指针的偏转,就像把孩子的身高画在门框上那样。因此,大脑和神经中的电活动强度不是以毫伏为单位记录的,而是以反射光束偏转的毫米数来度量。请注意,这束指示光不是激光笔。小镜子挂在优雅的抛光黄铜和木制装置内部,它反射的是火光。

图11 阿道夫·贝克在他的早期实验中使用魏德曼检流计记录了脑电活动。在此期间,出现过各种版本的检流计。这里显示的是达松伐耳检流计。请注意悬挂在扭弦上的那面圆形小镜子,它可以将光束反射到刻度尺上,读数大小与测量到的电信号成比例
由古斯塔夫·海因里希·魏德曼、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和约翰·丁达尔设计的魏德曼检流计在1874年开发成功时,是同类测量电压变化的仪器中最先进的。1886年,年轻的阿道夫·贝克进入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今天的雅盖隆大学),在著名的波兰生理学家拿破仑·齐布尔斯基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贝克在研究中就使用过这种检流计。[41]另一个研究神经系统电活动所必需的设备是电极,这在19世纪也是一个难题。金属电极与生理盐溶液(这样才能导电)接触时,会产生严重的电池效应。这些电极因电化学反应而产生电压,于是会干扰神经组织产生的微弱电活动的记录。事实上,意大利科学家亚历山德罗·伏打(1745—1827)和路易吉·加尔瓦尼(1737—1798)关于人体是否会产生生物电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质疑者认为所谓的生物电只是因金属探针接触裸露的神经而产生的人造电池效应,就像锡纸碰到金属锉会产生振动一样。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人们用非金属电极或浸泡在盐溶液中的纸和织物来接收肌肉、神经和大脑产生的微弱生物电信号。阿道夫·贝克在论文中描述了他使用的电极:“这些(电极)是用黏土浸在1%氯化钠溶液中制成的,它们插在装有硫酸锌溶液的玻璃管中,然后用锌丝连接到魏德曼检流计上。”[42](贝克的理论研究显然遇到了之前提到过的电池效应的问题;氯化钠就是食盐,而硫酸锌是一种膳食补充剂——两者都可以在现代厨房的橱柜中找到。)
阿道夫·贝克开始了他对青蛙的研究。他仔细地解剖青蛙,把它的大脑、脊髓和后腿暴露出来。贝克将青蛙的腿绑扎好后放在钟形玻璃罩内,里面放上潮湿的棉花,用来增加空气湿度,延缓组织干燥——它看起来就像一道野鸡大餐。与检流计相连的黏土电极被小心地放在青蛙的大脑上,然后用电脉冲刺激腿部坐骨神经,并用电极记录电脉冲造成的反应。电脉冲是由一个感应线圈产生的。它是缠绕在一个圆筒上的导线圈,这组线圈外面还有另一个缠绕导线的圆筒,外部的线圈比内部的线圈多。内部线圈由自制电池供电,当电池与线圈之间的连接断开时,其周围的电场突然消失,这个力使外部线圈突然产生电子振荡,从而产生比电池高得多的瞬时电压。现代汽车的发动机点火的工作原理也一样:当电池和感应线圈内部流过的电流随活塞运动反复通断时,汽车电池产生的12伏电压会在外部线圈中转变为2.5万伏的瞬时高压电脉冲,并在发动机的火花塞上产生强火花。
准备好青蛙和检测设备,贝克开始了他的实验。他充满期待地注视着从检流计射出的光束。他接通了感应线圈的电流以刺激坐骨神经——光束弹了起来!微小的偏转表明,青蛙大脑中与贝克的黏土探测电极接触的部位正在产生电能,这是由于坐骨神经受到电击而引发的。贝克将电极移动到大脑和脊髓的各个区域,并刺激不同的感觉神经,于是,他找到了大脑中处理不同感觉的位置。
在这个实验中,贝克提出了一个更为本质的发现:他注意到,即使没有刺激神经,光束也会剧烈地振动。许多人会认为这些微小的振动是精密测量系统固有的噪声,但是贝克敏锐地得出结论说,他看到的是大脑内涌动的电流所引起的自发性电振荡。他在189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写道:“我们研究的是神经中枢的自发兴奋。”[43]简而言之,这就是脑电波。

图12 狗的大脑对视网膜的光刺激和对前腿的刺激产生电反应的曲线图。这是阿道夫·贝克的博士论文里面的实验,该论文于1891年发表。电信号会引起检流计内部的一根细丝发生轻微扭转,细丝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镜子可以把反射光束投射到刻度尺上,通过望远镜可以读取刻度
贝克把实验对象从青蛙换成了兔子和狗。他从动物头部的一侧打开颅骨,露出动物的大脑。他发现,当他给动物施加不同的感觉刺激时,动物大脑皮质的特定部位会出现电活动的突然变化:
用光刺激视神经,用声音刺激听觉,用感应电流刺激皮肤的不同感觉神经。为了刺激眼睛,我使用了一条燃烧的镁带。镁带通过特殊的机械装置移动,以使镜子反射到眼睛的火光保持恒定。[44]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感觉刺激不但没有增加正在进行的电活动的强度,反而使它减弱了。每次实验,贝克都发现感觉输入抑制了动物大脑皮质中原本持续的电活动。我们现在知道,在施加感觉刺激后,大脑皮质内正在进行的脑电波活动变得不同步了。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在泳池边有节奏地往池壁划水一样,最终会产生巨大的波浪,但是如果两个孩子同时以不稳定或“不同步”的节奏划水,那么在水面上产生的波纹就会变小,而且不规则。新的感觉输入以某种方式扰乱了大脑之前由同步电活动产生的较大幅度的振荡。
贝克凭借出众的才华,用最原始的装置就做出了两个基本的发现:一个是他检测到了由感官进入大脑的信号所引起的脑电活动;另一个是他正确地意识到,大脑皮质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产生节律性的电活动,这种持续的电活动会受到感觉输入的干扰。他认为,“有理由相信,对某些中心的刺激会导致其他中心的活动受到抑制……因此,这些受到抑制的中心一定存在某种固有的活动状态,而且被抑制的只是这种内在的固有活动”。[45]大脑这种有趣的反应让他在后来提出了通过控制这些脑电波来止痛的想法,这是今天的前沿研究。经颅直流电刺激和带有植入电极的脑深部电刺激(DBS)都已被用来抑制某些部位的脑电波,以调节疼痛感。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感觉和认知活动会使脑电波突然去同步化。贝克的这一发现已被用于脑机接口(BCI)的开发,从而使人们仅凭思考就能够控制假肢。
这些由阿道夫·贝克(以及我们即将介绍的其他人)在波兰进行的开创性实验,揭示了动物大脑中的电磁波,这启发了汉斯·伯格在人的头皮上记录电活动的尝试。阿道夫·贝克将他的研究对象从青蛙、兔子和狗扩展到猴子身上,它们都表现出相同的脑电波反应。对于贝克来说,下一步可能就是用人类做实验了。但很不幸,他进行研究的地方正好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国际冲突的中心。在脑科学刚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时刻,贝克的研究因政治事件、战争和偏执而被搁置。
1895年,贝克接受了利沃夫(Lwów)大学新成立的生理学系主任的职务。当时波兰已被瓜分,利沃夫市归属奥地利。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动荡中,利沃夫市被多次易手。20世纪初,它成为波兰、乌克兰和犹太文化的多元化中心,也是许多波兰民族社团和第一份意第绪语日报的故乡。但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座城市被俄国人占领了。波兰人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独立性,这使得波兰学者实际上充当了抵抗俄国占领和统治的反抗者角色,并对俄国的统治构成了威胁。波兰被入侵的第二年,贝克与其他9位杰出公民在从德奥联军占领区撤退时被俄国人绑架,并被送到基辅当人质。
贝克在被囚期间曾经写信给著名的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教授,后者最著名的研究是让狗听见铃声就流口水。贝克请求巴甫洛夫为他向俄国当局辩护。1916年,在被囚禁了两年之后,阿道夫·贝克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安排的一次人质交换得以返回利沃夫,他对巴甫洛夫的营救心存感激。然而,1916年的利沃夫仍处在战争的前沿,此时已被乌克兰军队包围(当时乌克兰还不属于俄国)。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利沃夫,紧接着又遭受了波乌战争和波苏战争的蹂躏。1919年,波兰赢得了自1795年以来的第一次独立,但是利沃夫一直是有争议的领土,直到1923年才被正式承认为波兰的一部分。
入狱后,贝克没有再继续他关于大脑电活动的研究,而是将注意力放到了生理学上。贝克和他的导师拿破仑·齐布尔斯基共同出版了一本生理学方面的教科书,随后他自己也专门出版了一本神经生理学的教科书。贝克继续在大学任教,是学术和文化团体的顶梁柱,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1930年,67岁的他退休了,但之后并没有得享安宁。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动荡再次爆发。作为回应,9月17日,苏联人也入侵波兰。9月22日,利沃夫市被苏联红军占领,并把利沃夫市改成了今天的名字Lviv。在此期间,利沃夫大学以一位乌克兰作家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乌克兰语被定为正式的教学语言。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许多波兰学者被免职,还有12名学者被苏联人杀害。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利沃夫市被德国人占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的纳粹死亡别动队对该市的犹太人进行了一系列屠杀。第一次屠杀是在乌克兰民族团体的帮助下进行的,约有7 000名波兰犹太人被杀害。第二次屠杀的目标是大约2 500名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怀有敌意的公民。除了策划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纳粹别动队在入侵一个国家后,还根据精心罗列的打击名单,有选择地清除异己。针对英国的暗杀名单被称为“希特勒的黑名单”,这本144页的小册子一共印制了2万册,列出了要追杀的2 820个人的姓名和详细信息。[46]德国入侵波兰后也印发了一套类似的黑名单。名单上不仅包括犹太人,还包括神职人员、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对希特勒的统治来说,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家、学者和科学家就像政治家和游击队一样危险。德国将军汉斯·弗兰克在德国入侵波兰后曾担任波兰总督,其间他写道:“波兰这片土地将变成知识分子的沙漠。”[47]身为知识分子、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贝克处境非常危险。
1941年7月3日,在纳粹别动队的指挥下,纳粹占领军逮捕了25名波兰学者及其家人。[48]他们把抓到的人带到一个经过改建的集中营,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拷打和审问,然后把他们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入侵波兰,当时大约有15万名犹太人居住在利沃夫市,其中包括9万名儿童。[49]到战争结束时,利沃夫的15万名犹太人几乎无一幸存。[50]利沃夫市西北郊的亚诺夫斯卡街134号,以前是一家工厂,后来被改建为集中营,有超过20万人在那里被杀害,阿道夫·贝克教授就是遇难者之一。
得知许多教授在利沃夫遭到屠杀后,贝克在大学附近的家中待了一年,拒绝逃亡。[51]在80岁生日即将到来时,贝克病倒了。德国人要把他从医院带到亚诺夫斯卡集中营。贝克的儿子是一名医生,他曾给全家人分发过氰化钾胶囊。贝克吞下了自己的致命药丸,选择结束生命,而不是被纳粹送进毒气室。[52]
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历史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灾难、破坏和死亡的旋涡,反复将当地的居民吸进去。今天,利沃夫已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但2014年,俄罗斯军队控制了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将其并入俄罗斯联邦,该地区再次陷入冲突。回顾神经科学发展初期的这些故事是想提醒人们,我们始终生活在历史的背景下,并且希望从中吸取教训。贝克所处的时代与现在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在利沃夫策划屠杀教授的一个盖世太保军官,在数十年后被发现用了一个假名居住在阿根廷,直到1985年才被捕,但他在被引渡之前便离世了。
理查德·卡顿
世界其实很小。离我家不远就是马里兰州的卡顿斯维尔,靠近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1720年,欧洲人最早开始在那里定居。1787年,卡顿家族也从英国搬到卡顿斯维尔居住。[53]1887年,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医学博士理查德·卡顿顺道拜访了他的祖先们所创建的这个小镇。他此行的目的是去参加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敦大学举办的会议。在会议上,他要就他的研究成果做报告。卡顿报告的题目是《脑灰质电现象的研究》。[54]

图13 英国医生理查德·卡顿(1842—1926)在对兔子和猴子的研究中,第一个发现了脑电波活动。这张照片是在他30岁左右拍的,那时他正在进行脑电波的研究
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关于大脑电流的论文虽然广受好评,但其实大多数人没看懂。”[55]
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使用不同的语言。这种相对隔离的状态造成的后果是,哪怕重要的发现也可能会被大型科学团体忽略。现在情况仍然没有变化,如果没有互联网或其他快速可靠的国际交流方式,那么这种忽视可能还会更常见。事实上,当阿道夫·贝克在1891年发表论文时,他根本不知道16年前在英国已经有人通过实验在兔子和猴子身上发现了脑电波。1887年,当理查德·卡顿在华盛顿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贝克刚刚开始他关于感觉刺激的电反应的研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卡顿早在12年前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卡顿在1875年的英国医学会会议上发表了他初步研究结果的简报。据这份简报描述,通过使用检流计,他成功地记录到了兔子和猴子脑部的自发电流:“我们发现感觉印象可以影响某些脑区的电流活动,例如,费里尔博士已证明与兔子眼睑运动有关的那部分脑区的电流会因为对侧视网膜受到光线的刺激而产生显著影响。”[56]这篇简短的文章详细记述了兔子脑电波的发现,但包括阿道夫·贝克在内,几乎没人知道它。
卡顿将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40只兔子、几只猫和猴子,并在1877年5月5日的《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对实验结果做了更全面的描述。他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所有被检查的动物大脑都有电流……电流通常处于恒定的波动状态;指针的波动通常很小,大约为20~50度;有时则可以观察到较大的波动,在某些情况下,动物的肌肉运动或心理变化会造成这种明显波动。”[57]但是,这些论文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般来说,那个时代的生物科学主要是由像卡顿这样的医学从业者来做的。他们通过行医获得收入,而他们的科研工作既没有收入,也很难出名。当时,生理学(更别提神经生理学)尚未被当成一门科学,也没有自己的学术机构、科学社团和学术期刊,而且卡顿的科研工作对医生来说几乎没有实用价值,也跟医学毫不相干。卡顿带着经过12年研究的成果参加了1887年的医学大会,然而那些听众还是未能理解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尽管卡顿的研究并未引起医学界的共鸣,但他始终是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和教授。1904年,他成为利物浦大学医学系的主任。
1890年,贝克发表了他论文研究的摘要,详细介绍了他对脑电波的记录,从而引发了关于谁最先发现脑电波的争论。俄国生理学家瓦西里·达尼列夫斯基声称自己在1877年的论文中记录了动物的脑电波,早于贝克的实验。他没有公布他的发现,而是将它们装在信封里密封起来,保存在位于维也纳的帝国科学院的一个地下室里。现代的科学协会和学术期刊可以记录和传播各个领域的发现,但在此前的时代,把研究结果藏在地下室这种保存科学发现的方式并不罕见。但在1891年2月,卡顿给《生理学杂志》(Centralblatt für Physiologie)写了一封信,指出他在1875年的论文击败了所有人。[58]他在信中说:“1875年,我在英国医学会生理学分会上做过一个演讲,向大家展示了温血动物的大脑能产生电流,并且明确了这些电流与脑功能有关。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注意这篇文章:《英国医学杂志》,1875年,第2卷,278页。”[59]

图14 第一个发现脑电波的是伦敦医生理查德·卡顿。卡顿于1875年8月在爱丁堡举行的英国医学会年会上宣布了他的发现,但这一成果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卡顿于1887年前往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乔治敦大学公布了有关他的研究的论文,但他的研究并不为人们所理解,这一发现也被历史遗忘。直到半个世纪后,阿道夫·贝克开始脑电波研究时,依然对卡顿的早期工作一无所知
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英国医学博士理查德·卡顿确实是第一个观察到脑电波的人。他在19世纪70年代就使用简单的设备在实验动物的大脑中发现了脑电波,但距离全世界承认这一重要成就为时尚早。1891年,49岁的卡顿辞去了教授职务,并放弃了对大脑电活动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与发热、中毒和肢端肥大症(一种巨人症)有关的医学问题。有趣的是,卡顿于1897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医学院大会,拿破仑·齐布尔斯基-阿道夫·贝克的导师——也出席了。[60]
理查德·卡顿于1926年去世,距离伯格开始人类脑电图研究不过两年。他不认识汉斯·伯格。伯格的发现于1929年首次发表,但是就像50多年前卡顿的第一个动物脑电图一样,这个成果一开始也被打入了冷宫。[61]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我们很容易指责那些没有看到卡顿演讲的意义的人,也很容易质疑为什么从发现动物脑电波到发现人类脑电波要花这么长时间。但你要知道,19世纪初,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一样通电的东西,卡顿和贝克认为大脑有电流通过的想法更可谓石破天惊。在与世隔绝的实验室里,一些古怪的科学家绞尽脑汁地从天上捕获电,或者自己制造电,思考这种自然力,但当时的大众对它一无所知。电就像今天的暗能量一样稀有而神秘。
[1] Berger, H. (1904) über die k?rperlichen ?usserungen psychischer zust?nde: Weiteree 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lehre von der blutzirkulation in der sch?delh?hle des menschen.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2] Berger, H. (1904 and 1907) über die k?rperlichen ?usserungen psychischer zust?nde: Weiteree 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lehre von der blutzirkulation in der sch?delh?hle des menschen. Jena,Germany: Gustav Fischer.
[3] Millett, D. (2001) Hans Berger: From Psychic Energy to the EEG.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44: 522–542.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75ca/ e9df1a8ddb0724b53e778cacbf4be8cae983.pdf.
[4] Berger, H. (1910)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Temperatur des Gehirns.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5] Berger, H. (1940) Psyche.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6] Radin, D. (2006) Entangled Minds: Extrasensory Experiences in a Quantum Reality. New York, NY:Paraview Pocket Books.
[7] La Vaque, T. J. (1999) The History of EEG Hans Berger: Psychophysiologist. A Historical Vignette. The Journal of Neurotherapy 3: 1–9.
[8] Berger, H. (1940) Psyche, 6.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9] Berger, H. (1929) über das Elektrenkephalogramm des Menschen. Archiv für Psychiatrie 87: 527–570.
[10] Lemke, R. (1956)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ans Berger.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8: 708.
[11] Ibid.
[12] Baltimore Sun, January 4, 1931: 33. https://www.newspapers.com/newspage/ 214988483/
[13] Burtt [sic], C. Psychology and Parapsychology. In Smythies, J. R., ed. (1967) Science and ESP. 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61–142. See also Mundle, C. W. K. The Explanation of ESP.Chapter 8 in Smythies, J. R., ed. (1967) Science and ESP.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
[14] Caldwell, W. E. (1959) Some Historical Notes and a Brief Summary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Findings of Ferninando Cazzamalli.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60: 121–129.
[15] Cazzamalli, F. (1925) Fenomeni Telepsichice E Radioonde Cerebrali. Neurologica 42: 193–218;Cazzamalli, F. (1929–1930) Esperienze, Argomenti E Problemi Di Biofisca Cerebrale. Quad. Di Psichiat.: 81–105; Cazzamalli, F. (1935) Di un Fenomeno radiante cerebropsichico (reflesso cerebropsicoradiante) come mezzo di esplorazione psicobiofisca. Giornale Di Psichiat. E. Di Neuropathol. 63: 45–56.
[16] Cazzamalli, F. (1935) Phenomenes electromagnetiques du cerveau humain en activite psychosensorielle intense et leur demonstration par des complexes oscillateursrevelateurs a triodes pour ondes ultracourtes. Arch. Internat. Dc Neurol. 64: 113–142.
[17] 1英尺= 30.48厘米。——编者注
[18] Association of Italian Science of Metaphysics. http://www.metapsichica.net/home /home.asp?sid={A92545DD-98F2-4C3F-8D4F-DE98369D46D3}&idca=3&idpa=1.
[19] Metapsychic, The Italian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A.I.S.M. (Associazione Italiana Scientifica di Metapsichica.) http://www.metapsichica.net/home/home .asp?sid={68F482E7-66FE-4EFE-BEEE A768C23A76C9}&idca=2&idpa=1.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20] Association of Italian Science of Metaphysics. http://www.metapsichica.net/home/ home.asp?sid={A92545DD-98F2-4C3F-8D4F-DE98369D46D3}&idca=6&idpa=1. Accessed 2018.
[21] Finkler, W. (1930) Die elektrische Schrift des Gehirns [The Electric Writing of the Brain]. Neues Wiener Journal 38: 7. See also Borck, C. (2005) Writing Brains: Tracing the Psyche with the Graphical Method. History of Psychology 8:79–94.
[22] Moses, D. A., et al. (2019) Real-time Decoding of Question-and-Answer Speech Dialogue Using Human Cortical Activity.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no. 3096. See also Musk, E., and Neuralink(2019). An Integrated Brain-Machine Interface Platform with Thousands of Channels. Bio Rxiv.https://www.biorxiv.org / content/10.1101/703801v4; and Hanson, T. L., et al. (2019) The“Sewing Machine” for Minimally Invasive Neural Recording. Bio Rxiv. https://www.biorxiv.org /content/10.1101/578542v1.
[23] Adrian, E. D.; and Matthews, B. H. C. (1934) The Berger Rhythm: Potential Changes from the Occipital Lobes in Man. Brain 57: 355–385.
[24] Ibid., Figure 3.
[25] Lemke, R. (1956)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ans Berger.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8: 708.
[26] Brazier, M.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 London: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114.
[27] Borck, C. (2005) Writing Brains: Tracing the Psyche with the Graphical Method. History of Psychology 9, 79–94.
[28] Berger, H. (1901) Zur Lehre von der Blutzirkulation in der Sch?delh?le des menschen namentlich unter dem Einfluss von Medikamenten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On the theory of the blood circulation in the human skull, especially under pharmaceutical influences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29] Fayed, N.; Modrego, P. J.; and Morales, H. (2006) Evidence of Brain Damage after High-Altitude Climbing by Mean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19: 168.E1–6.
[30] Fields, R. D. (2009, September 30) Are the Mountains Killing Your Brain? Outside. https://www.outsideonline.com/1884846/are-mountains-killing-your-brain.
[31] 1英里= 1.609 344千米。——编者注
[32] 1码= 0.9144米。——编者注
[33] Lemke, R. (1956)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ans Berger.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8: 708.
[34] Goldensohn, E. D. (2001) Cellular Electrical Phenomena in Focal Epilepsy. In Luders, H. O.; and Comair, Y.; eds. Epilepsy Surgery, 2nd ed. Philadelphia, PA: Lippincott and Williams and Wilkins, 1–18.
[35] Niedermeyer, E. (2005) Historical Aspects. I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Basic Principles,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Related Fields, 5th ed. Philadelphia, PA: Lippincott Williams and Wilkins, 1–16.
[36] Das 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 Reichsgesetzblatt, Part I, July 14, 1933: 529;reprinted in Meier-Benneckenstein, P.; ed.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lume 1: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1933, edited by Axel Friedrichs. Berlin, 1935: 194–95.
[37] Forced Sterilization,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https://www .ushmm.org/learn/students/learning-materials-and-resources/mentally-and -physically-handicapped-victims-of-the-nazi era/forced-sterilization.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38] Redies, C.; Viebig, M.; Zimmermann, S.; and Frober, R. (2005) Origin of Corpses Received by the Anatomical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Jena During the Nazi Regime. The Anatomical Record Part B: The New Anatomist 285B (1): 6–10. Redies, C.; Frober, R.; Viebig, M.; and Zimmermann, S. (2012) Dead Bodies for the Anatomical Institute in the Third Reich: An Investig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Jena. Annals of Anatomy 194 (3): 298–303. doi: 10.1016/j.aanat.2011.12.004.
[39] Pierre Gloor states that at this time, before the existence of brain imaging technology, surgeons would sometimes stick probes in the brain in an attempt to localize tumors. Gloor, P. (1969) Hans Berger on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of Man. New York, NY: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5.
[40] Fields, R. D. (2011) Imaging Learning: The Search for a Memory Trace. The Neuroscientist 17: 185–196.
[41] Chapman, H. C.; and Brubaker, A. P. (1888) Researches upon the General Physiology of Nerve and Muscle No. 2.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 40: 155–161. http://www.jstor.org/stable/pdf/4061244.pdf.
[42]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30.
[43] Beck, A. (1891) The Determination of Localization in the Brain and Spinal Cord by Means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Doctoral thesis published in Polska Akademija Umiejetno?ci 2: 187–232.
[44]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 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33. Beck, A. (1891) The Determination of Localization in the Brain and Spinal Cord by Means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Doctoral thesis published in Polska Akademija Umiejetnosci 2: 212.
[45]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33. Beck, A. (1891) The Determination of Localization in the Brain and Spinal Cord by Means of Electrical Phenomena. Doctoral thesis published in Polska Akademija Umiejetno?ci 2: 187–232.
[46] Hitler’s Black Book—List of Persons Wanted. Forces War Records. https://www .forces-war-records.co.uk/hitlers-black-book.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47] The Polish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43) The German New Order in Poland.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432, quoted in Wrobel, P. (2000) The Devil’s Playground: Poland in World War II. Montreal:The Canadian Foundation for Polish Studies of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 Sciences. http://www.warsawuprising .com/paper/ wrobel1.htm.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48] Kr?tosz, J. Likwidacja kadry naukowej Lwowa w lipcu 1941 roku. In Heska- Kwa?niewicz, K.; Ratuszna,A.; and ?urawska, E., eds. (2012) Niezwyk?a wi?? Kresów Wschodnich i Zachodnich. Uniwersytet ?l?ski:13–21. Retrieved December 12, 2014. http://wydawnictwo.us.edu.pl/node/2822. See als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acre_of_Lw%C3%B3w_professors.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49]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L’viv. http://www.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Lviv.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50] Nagorski, A. (2015). The Greatest Battle.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83.
[51] Coenen, A.; and Zayachkivskar, O. (2013) Adolf Beck: A Pioneer i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in Between Richard Caton and Hans Berger. Advanc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9: 216–2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02832 / pdf/acp-09-216.pdf.
[52]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48. 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nowska_concentration_camp.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19.
[53] U-S-History.com. History of Catonsville, Maryland. https://www.u-s-history.com/pages/h2789.html.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9.
[54] Caton, R. (1887) Researches on Electrical Phenomena of Cerebral Grey Matter.Ninth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gress 3: 246–249.
[55]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16.
[56] Ibid., 7.
[57] Ibid. Also Caton, R. (1877) Interim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Electric Currents of the Brain.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62–65.
[58]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62.
[59] Caton, R. (1891) Die Strome der Centralnervensystems. Centralblatte der Physiology 4 (1890–1891):785-786, translated by Brazier, ibid., 62, in reference to his prior paper, Caton, R. (1875) The Electric Currents of the Brai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 278.
[60] Brazier, Mary A. B. (1961) A History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First Half-Century.London: Pitman Medical Publishing Co., 20–21.
[61] Berger, H. (1929) über das Elektrenkephalogramm des Menschen. Archiv für Psychiatrie 87: 527–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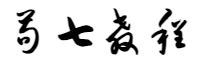
本文暂时没有评论,来添加一个吧(●'◡'●)